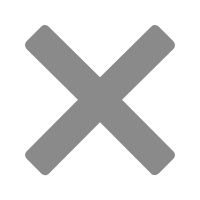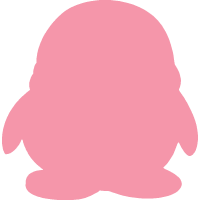第28章 他受伤了
苏绵悄悄观察宋景和,没想到他居然是真的在看花魁,表情还十分认真。
宋景和看着花车上的花魁,却没有忽视她看向自己的目光,语气从容地问:“苏姑娘不是喜欢看花魁吗?怎么不看了?难道是觉得我比花魁还要好看?”
这厮也忒自恋了吧?苏绵没忍住偷偷翻了个白眼。
思忖间,一缕极淡的血腥味钻入鼻尖,苏绵鼻翼轻动,眉心微蹙,血腥味?
这是从何而来的血腥味?
鼓乐骤歇,红木花车像被晚风推醒的巨兽,慢吞吞地调头,向东街迤逦滑去。
车檐垂下的绸纱被夕阳染成流霞,层层叠叠地飘起,像一条不肯落地的云河。
苏绵乍一闻到血腥味,便立刻从胡姬阿娜身上收回目光。
那味道像被雨水浸过的旧铜,带着微涩的腥甜,从喧嚣里笔直地刺进她的呼吸。
她的嗅觉一向灵敏,左右闻一闻,便发现了血腥味的来源。
她循味望去,目光落在宋景和垂在身侧的左腕,护腕的暗纹已被湿意洇得更深,像暮色悄悄爬上雪刃的边缘。
她心头一紧,低声问:“宋大人,你受伤了?”声音轻得仿佛怕惊动那抹血色。
“无事,小伤而已。”宋景和微抬下颌,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,像寒星落入深潭。
下一瞬,绣春刀已离鞘,寒光划出一弯冷月,直指花车背后那团锦绣花球。
尖锐的刀锋没入花球,花瓣簌簌四散,殷红的血水顺着刀背滴落,像胭脂化雪,又像暮春最后一瓣桃花零落成泥。
围观的人潮骤然屏息,随即爆出一阵低低的惊呼,如潮水拍岸:“这是血吗?花球里面难道有人?”
众人面露恐惧,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,但好奇心又促使他们留在原地。
花球缓缓破裂,露出的不是花蕊,而是蜷缩在里面的一个男子。
“真的有人!”
“他怎么会藏在花球里?”
众人又是一阵诧异惊呼,直愣愣地盯着人看。
花魁阿娜和男子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震惊,仿佛对此早已知情,但脸色却难看至极。
花球中的男人瘦骨支离,衣染尘血,十指指甲尽落,指尖血肉模糊,腰腹短箭未拔,箭羽在风里微微颤抖,面色惨白,却仍掩不住旧时清隽的轮廓。
他身上的血珠沿着短箭滚落,溅在木板上,看得人心惊肉跳。
旧伤如此严重,眼下又添新伤。
宋景和的绣春刀正好刺中男子左肩,血流不止。
苏绵只觉心口骤然一紧,仿佛有人把冰碴子塞进胸腔,寒意顺着血脉爬遍四肢。
她不忍细看,只把视线虚虚地掠过那团蜷在花球里的身影,便已觉痛意钻骨,若这些伤落在自己身上,只怕连呼吸都要打颤。
宋景和这人果真心狠手辣,一出手便让人见了血。
胆战心惊的同时,苏绵又忍不住好奇,这个人到底是谁?
为何宋景和不问缘由便拔刀刺去?
疑问像雨前闷雷,轰隆隆在脑海里滚过。
宋景和不会无故向花球动刀,他向来以刀尖量罪,既出鞘,必是窥见了藏匿的恶、或逃匿的囚。
她忽然想起今晨在北镇抚司外听见的只言片语,“秦家尚有一息未绝,昨夜自永兴巷遁走,身负重创”。
电光石火间,一个念头劈进心底,莫非花球中的男子,正是那位传言已死的秦家六公子?
只是她并未见过秦家六公子,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。
但下一秒,百姓们的窃窃私语很快印证她的揣测。
人群中爆发出阵阵议论,声音如碎瓷落地。
“那不是秦六郎吗?不是说他已经被斩首示众了吗?怎会自花球里爬出?”
“你还不知道哇?听说他是在行刑前夜逃走了,说来他也厉害,能在诏狱里逃出来,官府这几日满城通缉的逃犯就是他。”
一人好奇道:“瞧他这副样子,难道是想借花魁游街混出城门?”
“八九不离十哦!”
“那可真是胆大包天!”
其中一个挑着扁担卖糖葫芦杂耍的瘦长脸插话道:“这个花魁阿娜一点都不吃惊,看样子她肯定是知道的。”
“也难怪她会同意出来游街,原来是想借机帮助秦家六郎逃跑,可真是不要命了!”
“若是让我知道了秦家六郎的消息,我立马就去上报官府领赏钱了!”
秦家结党营私之事,京城百姓都有所耳闻,此案虽已结案处理,但仍有许多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。
“秦家真的会犯结党营私之罪吗?万一是被人冤枉的呢?”
“难保没有这个可能!秦家在京城可是有名的良善之家,两年前京城周围的县衙遭遇洪灾饥荒,难民纷纷涌进京城,秦家第一时间开仓赈灾,为难民搭建临时住宿的帐篷,请大夫给他们治病,不仅救了许多人的命,还为朝廷挽救了不少损失。”
“切!达官显贵之家又不是没有表面良善实则险恶的,他们此举不过是为了赢得民心而已,骗的就是你们这些人。”
持不同意见的两拨人忽然就为了秦家此事吵得面红耳赤。
议论声浪里,突然又掺进一句大声的嚷嚷:“各位各位,我想起一件事!”
“这个花魁阿娜可是秦家六公子的红颜知己,那秦公子以前经常出入青楼,两人常常以诗对弈,以棋会友,还一度成为咱们京城的一段佳话呢!”
“没错!你不说我都忘了,的确是这样的!秦家六公子与这个花魁关系可不一般!”
一个官宦人家的贵公子隔三岔五去青楼找花魁,不是贪恋美色,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,仅仅只是弹琴对弈,吟诗作画,传出去都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
“那这个花魁也算是对秦六公子有情有义了,居然敢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去帮他,秦六公子也真是上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。”
卖糖葫芦的瘦长脸挑着扁担,高声插话:“情义能值几个钱?知情不报可是同罪,换我早去领赏银了!”
旁边老妪却摇头:“谢家当年开仓放粮,救我一家老小,怎会是罪人?兴许真有冤情。”